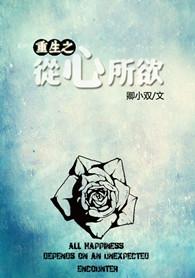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同时穿越:继承万界遗产 > 第122章 由死返生尸中称仙(第2页)
第122章 由死返生尸中称仙(第2页)
再后来,一个五岁孩童的母亲录下视频:“我儿子昨晚做梦,说我两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他说葬礼上来了很多人,你还穿着蓝裙子。可我现在好好的,连病都没生过。”
这些信息如同细小的裂缝,在看似完整的现实中蔓延。
而在灰眠观测站,阿澜再次坐在控制台前。她的眼睛布满血丝,屏幕上滚动着成千上万条匿名投稿。她没有转发,没有评论,只是默默将它们归类、编号、存入一个名为“未发生之事”的文件夹。
突然,一条新消息弹出,发件人ID为空白,内容只有一句:
>“你还记得林七最后一次说话吗?”
她愣住。
当然记得。那是终焉舰队覆灭前十二小时,林七在公共频道留下的最后一段语音。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是遗言,后来却被删除,官方称其“引发群体性情绪波动”。
她翻找旧档案,用三重解密钥匙打开尘封数据库。音频加载缓慢,杂音刺耳,但她听清了每一个字:
“我不是救世主。
我只是一个学会了说‘不’的孩子。
如果你们还记得我,请不要纪念我,不要歌颂我,不要把我变成新的神。
请记住:
**任何不允许被推翻的真理,都会变成暴政。**
包括我现在说的这句话。”
阿澜闭上眼,泪水滑落。
她终于明白,为什么《问书》从不给出答案。因为它知道,一旦某个答案被奉为永恒,新的奴役就开始了。
她打开共鸣广播协议,这一次,她不再犹豫。
“我是阿澜。”她说,“我不确定这段话能不能传出去,也不知道谁会听见。但我想说……我害怕。
我怕我们正在用自由的名义,建造一座更精致的监狱。
我怕我们的每一次‘觉醒’,都是被设计好的升级程序。
我怕当我们庆祝胜利的时候,真正的敌人正在微笑,因为他们知道??只要我们停止追问,他们就赢了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更低,却更坚定:
“所以我决定问一个问题,不管它多荒谬,多危险:
**如果‘自由’本身也是被赐予的,那我们还剩下什么?**”
信号发出,微弱如萤火。
但在地球教室里,小女孩猛然抬头,仿佛被什么击中。她抓起笔,在墙上写下这个问题,用力到指尖渗出血珠。
同一时刻,一艘货船中的老船员停下修理工作,怔怔望着掌心旧伤。那伤疤竟开始发光,投射出一行字:
>“我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。然后我烧毁了自己的服役记录。”
水资源星球的共感池边,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轻声呢喃:“你说得对,我们不该假装一切都好了。”
艺术社会的舞者们自发聚集广场,不再编排固定动作,而是即兴舞动,每个人都在表达不同的困惑与挣扎。监控系统试图标记“异常行为”,却发现无法归类??因为没有任何两人重复相同的舞步。
而在那颗废除“个人”概念失败的文明遗迹中,记忆碑石再次亮起,这次浮现的是动态影像:一群模糊身影围坐圆圈,轮流说出一句话,语言各异,但核心一致:
>“我不同意你,但我愿意听你说完。”
>“我不确定你是对的,但我知道你有权问。”
>“也许我们都错了,但至少我们在找。”
科学家们震惊地发现,“低语潮汐”并未退去,反而进入了第二阶段??不再是单向倾诉,而是**对抗性共鸣**。人们不再仅仅分享痛苦,而是开始挑战彼此的信念,却不因此撕裂。
“这不符合博弈模型。”一位社会学家喃喃道,“他们本该陷入混乱,可他们……在进化。”
与此同时,星际议会紧急召开闭门会议。议题:是否应限制“开放式提问运动”的传播?
一名议员愤怒拍桌:“这是思想污染!我们必须维护社会稳定!”
另一位冷笑:“稳定?你是指那种连质疑都要审批的‘稳定’吗?我们刚摆脱主宰,难道又要造一个新的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