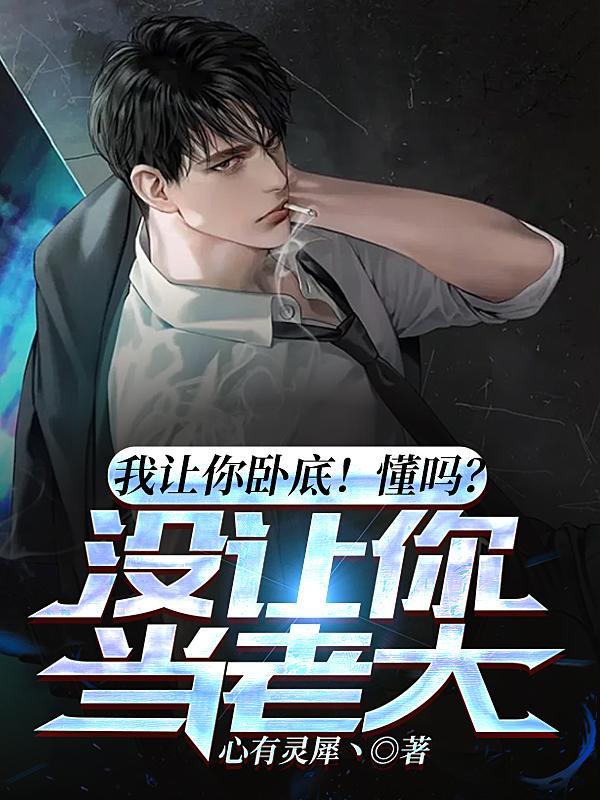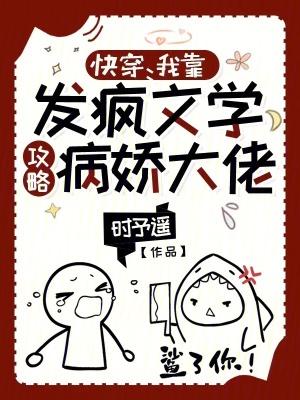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魏晋不服周 > 第204章 不装了(第1页)
第204章 不装了(第1页)
第二天一大早,石守信就步行离开了李氏的宅院,前往晋王府。
此刻他感觉浑身轻松,因为接下来,再不必去跟那些老登们打交道了。
也可以暂时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,避开这里浑浊到令人作呕的政治氛围。。。。
驼铃摇曳于残阳之下,黄沙尽头,天与地熔成一线。阿禾坐在头驼之上,左手按着竹箧,里头收着临行前百姓所赠的信札??有老农写下的“学会了‘状告’二字,我要去县衙讨回被夺的水渠”;有婢女偷偷托僧人转交的纸条:“读了《婚姻律》,我明日便拒嫁那酒糟鼻的老财主。”最让她心头一颤的,是一张用炭笔涂在破布上的画:一个女人站在高台,背后是无数举手的人,底下歪歪扭扭写着:“阿禾娘娘讲法,我们不怕了。”
晓禾策马而来,风卷起她半边发髻,露出额角一道旧疤??那是三年前在玉门关外,为护一名识字孩童被马贼铁鞭扫中的痕迹。“后队清点完毕,十二车简册无损,三十七名随行学子皆安。乌仁娜说,北道上已有六处驿站挂出了‘微学堂’的木牌,虽只是几块破板子钉在土墙上,可孩子们已经在学‘人人生而自由’这句了。”
阿禾点头,目光却落在远处一道孤影上。那是张守文,独自步行于沙丘之间,手中铁杖每一步都深深插入沙中,仿佛在丈量这片沉默千年的土地。自国子监那一日之后,他再未说过一句话。不是不能说,而是不愿说。他的喉咙在早年受刑时被烙过,声带如枯藤缠绕,每一次发声都像刀割肺腑。可那日他在祭典上朗读律文时,竟一字不差,声震屋瓦。众人后来才知道,他是以腹语借铜筒扩音,靠的是十年如一日的苦练。
“他还在想王允之最后那句话。”晓禾低声说,“‘皮已尽,骨将现’……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
阿禾望着远方渐沉的落日,轻声道:“皮是遮羞的,是礼教、是门第、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说辞。骨,是权力本身。他说的不是预言,是坦白??他们已经不在乎伪装了。下一次,不会再是清场,而是斩根。”
话音未落,前方沙尘骤起。一骑快马疾驰而来,马背上的少年满脸风霜,竟是敦煌学院派出的传信童子。他滚落下马,跪地呈上一封泥封竹筒。阿禾拆开一看,脸色微变。
“出事了?”
“敦煌失火。”阿禾声音平静,却让四周空气骤冷,“昨夜亥时,藏书阁遭焚,半数典籍化为灰烬。纵火者留书于墙:‘妄议朝纲者,书亦当诛。’”
晓禾猛地攥紧缰绳:“是谁?王允之的人追到了西域?”
“不。”阿禾摇头,“火是从内部烧起的。守阁的老仆陈伯被人发现昏倒在井边,手里攥着半块腰牌??是学院自己人干的。”
众人默然。信仰可以点燃人心,也能腐蚀人心。有人因光明而追随,也有人因恐惧而背叛。那个曾跟着阿禾抄写《教育权》全文的年轻助教李元朗,三日前请假回乡探母,至今未归。而他掌管着藏书阁夜间钥匙。
“我们回去吗?”乌仁娜策马赶到,巨幡卷在背上,像一面未降的战旗。
阿禾沉默良久,忽然笑了:“回去?不。我们继续走。但走得更慢些,让消息飞得更快些。”
她转身召集众人,立于沙丘之上,声音清晰如刃:“从今日起,火种队分三路行进。第一路由晓禾带队,沿河西走廊南线,经鄯善、且末,设立七座流动讲坛,主题为‘如何识别伪律’;第二路由乌仁娜领二十人北上伊吾,联络戍边营与胡部首领,宣讲《边民平等赋权令》;我与张守文率余众缓行中央大道,每五里设一‘问答桩’??木桩刻问题,路人可用炭笔作答,三日后派人回收整理,汇编成《民问录》。”
“这是做什么?”有人不解。
“我们在收集证据。”阿禾目光如炬,“王允之以为烧一本书就能熄灭火种,可他知道吗?真正的律法不在竹简上,而在千万人心里。当一个人开始问‘为什么税要交三成’,当一个母亲敢说‘我女儿也要上学’,法律就已经活了。我们要做的,不是重建藏书阁,是让每一颗心都成为移动的图书馆。”
队伍依令分兵。三日后,第一份《民问录》送至阿禾手中。厚厚一卷沙纸装订而成,问题五花八门:“官府征役为何总抽穷户?”“寡妇改嫁要罚钱,是不是违法?”“孩子识字,算不算政绩?”更有稚嫩笔迹写道:“老师说‘君要臣死’是对的,可阿禾姐姐说不对,谁说的是真律?”
阿禾连夜提笔批注,逐条引用《正始律》原文回应,并命人誊抄百份,随商队送往各地微学堂。她在卷首写下一句:“疑问即觉醒,记录即反抗。”
与此同时,晓禾一行抵达鄯善。当地豪族早已听闻“妖言惑众”的传言,闭门不出,还煽动市井泼皮阻拦讲学。晓禾不怒不争,只在城东闹市摆下“盲判台”??请十名不识字的老农,蒙眼听两段陈述:一段是豪强借口“祖制”强占水源的辩词,一段是村民依据《水利均享律》的申诉。然后让他们判断谁更有理。
十人中有九人指认豪强无理。晓禾当场揭开蒙布,指着律文道:“你们没读过书,可良心懂法。法律不是用来吓人的,是用来保护弱者的。”围观百姓哗然鼓掌。当晚,三十六户人家自发组织“夜读班”,由一名曾赴敦煌受训的货郎任教。
而在北疆,乌仁娜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敌意。伊吾守将起初拒不相见,称“军中不谈民政”。她便在营外扎营三日,每日清晨击鼓诵《戍边士兵权益十六条》,诸如“战功应记实名,不得冒领”“阵亡抚恤须直付家属”“伤病不得弃于荒野”。许多老兵闻声而来,默默伫立风中。
第四日清晨,一名断臂老兵拄拐而出,颤声问:“这些……是真的?”
“是真的。”乌仁娜取出青铜板拓片,“而且,你们有权要求兑现。”
当夜,守将秘密来访,坦言自己也曾是微学堂学生,只因得罪上司被贬边陲。“我本已麻木,可听见你念‘士兵非牲畜’那一句……眼泪就下来了。”他承诺协助传播律文,并提供一份名单:近三年有二十三名士兵“失踪”,实为被长官贩卖为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