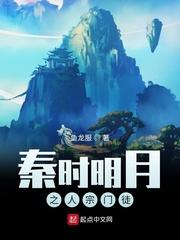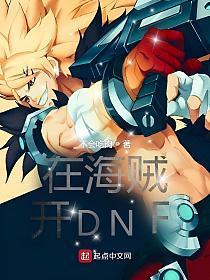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大明第一国舅 > 第646章 不成器的小辈太多了(第1页)
第646章 不成器的小辈太多了(第1页)
不得不感慨朱标这小子确实够坏。
他师从大儒,伴读是冯诚、花炜这样的功臣之后,以及一些德行不错的才俊。
看看他现在给朱雄英选的伴读或者侍讲等,浙东四先生的子孙。
这放出去能堵不少人的嘴。。。
正旦的钟声还在紫禁城上空回荡,天边刚泛起鱼肚白,朱标便已起身更衣。李贞跟在他身后,小脸绷得紧紧的,冕服上的玉佩叮当作响。马寻站在廊下,望着这对父子并肩而行的背影,嘴角微扬,却也掩不住眼底那一丝忧虑。
昨夜宫中设宴,诸命妇齐聚坤宁宫为马秀英贺节,席间蓝氏悄悄拉住国子学的手,低声道:“你家那小子,如今可是雄英身边最亲近的人了。”国子学只是笑而不语,心里却明白,这份亲近既是荣耀,也是重担。刘?尚未入京,但朝中风向已然微妙??徐达、傅友德这些老将虽仍受礼遇,可文官集团对里戚干政的警惕从未消减。
“爹,我紧张。”李贞忽然小声说。
朱标低头看他一眼,伸手替他扶正冠缨,“怕什么?今日你是去读书,不是上刑场。”
“可……可那么多双眼睛盯着。”李贞攥着袖口,声音越来越轻,“姑母说,伴读不只是陪太子读书,还得懂分寸、知进退,一句话说错,就可能连累全家。”
朱标脚步一顿。
他转头看向儿子,目光深邃如古井,“这话是谁教你的?”
“是姑母。”李贞低声答,“还有舅母马寻夫人,她让我记住三件事:一不妄议朝政,二不结党营私,三不在宫中传话。”
朱标沉默片刻,终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,“记住了,很好。但你要知道,伴读之责,不在谨言慎行,而在辅弼君德。雄英将来是要治天下的人,你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,才是他最信得过的人。所以不必畏首畏尾,只求问心无愧。”
李贞重重点头,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
此时已至午门,百官列队等候大朝仪开始。朱标牵着李贞缓步前行,沿途不断有人拱手致意。汤和远远看见,咧嘴一笑,挤开人群迎上来:“太子今日亲自送子入学,可是要给国子学添几分体面?”
“颍川侯说得不错。”朱标笑道,“不过不是我送子,是我带侄儿去见世面。”
汤和一愣,随即哈哈大笑,“好一个‘带侄儿’!这称呼改得妙啊,既显亲厚,又避嫌隙,难怪陛下常说你有帝王之度。”
两人相视而笑,暗流却不曾停歇。
国子监大门前,已有数十名学子肃立迎候。监丞戴元礼身穿青袍,手持笏板立于阶前,神情庄重。见到朱标一行到来,忙率众行礼。朱标还礼后,目光扫过那些年轻面孔,心中感慨万千。
这些人里,将来必有执掌一方的大员,也有因言获罪的贬臣,更有默默无闻终老讲坛的寒士。而此刻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,皆是对功名与理想的渴求。
“今日太子亲临,乃天家重学之举。”戴元礼朗声道,“请太子赐训词,以励诸生。”
朱标微微颔首,上前一步,清了清嗓子:“诸位皆国家栋梁之材,读书非为科第,实为济世安民。朕常听母后言,治国如烹小鲜,火候稍差,则味败矣。尔等当以德行为本,实务为用,勿尚空谈,勿逐虚名。他日若能为民请命、为国分忧,便是不负所学。”
话音落下,全场肃然。
李贞站在父亲身后,听得心头激荡。他知道这番话看似平和,实则暗藏锋芒??尤其是“勿尚空谈”四字,直指近年来士林中悄然兴起的清议之风。朱元璋严禁结社议政,而今太子亦以此警示学子,可见朝廷对此事何等忌惮。
仪式毕,朱标携李贞步入明伦堂。此处乃国子监核心所在,正中悬挂御笔“明德新民”匾额,两侧楹联正是那副引发争议之作:
**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”**
戴元礼见朱标凝视对联,神色微变,连忙解释:“此联原为前年某江南举人所献,臣等初觉其意甚佳,故悬于此处。后经陛下谕旨提醒,现已准备撤下。”
朱标摆手制止,“不必急着撤。这联本身无过,关键在如何理解。若以此激励学子心怀天下,何尝不是美事?只怕有人借题发挥,以讲学为名,行结党之实。”
戴元礼躬身称是。
正说着,忽闻外头一阵骚动。一名小吏慌忙跑进来禀报:“启禀监丞,青田刘家遣使递帖,言刘琏携弟刘?已于城外驿站候旨,请示是否准许入监觐见!”
朱标眉梢一挑。
刘琏身为刘伯温长子,素有才名,早年曾任翰林院编修,后因父罢官归隐而辞职返乡。如今突然携弟来京,且点名要入国子监,显然别有用意。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朱标淡淡道,“既是读书人,便按规矩办。”
不多时,两道身影出现在门口。前方一人约莫二十出头,面容清癯,举止沉稳,正是刘琏;其后少年十四五岁年纪,眉目俊朗,眼神锐利,行走间自带一股傲气,想必就是刘?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