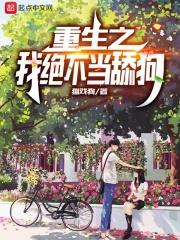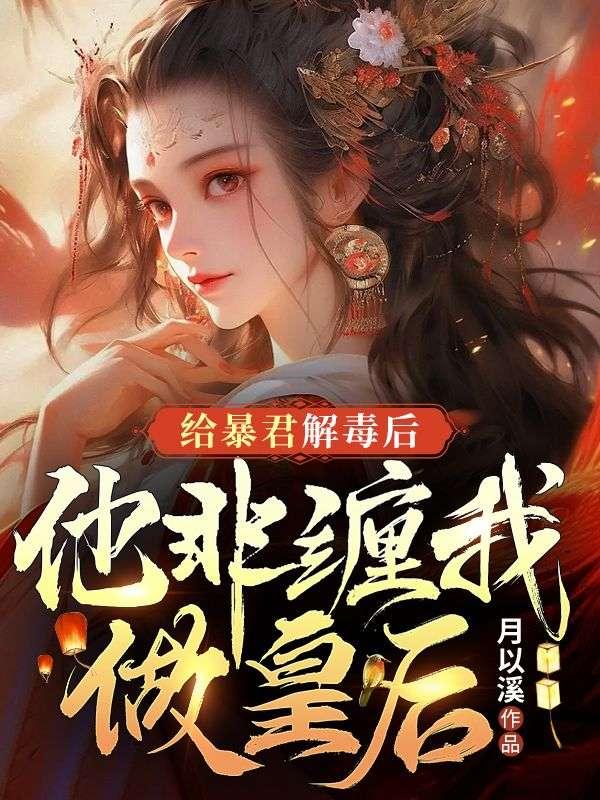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快婿 > 357重镇(第2页)
357重镇(第2页)
数月后,西域伊州废墟附近出现一名女子身影。她独行于荒漠,随身仅携一铃一卷,每至一处残破庙宇或废弃驿站,便取出颜料,在墙上绘下一羽残凤,题曰:“仁凰不灭,为民而醒。”
百姓见之,纷纷效仿。有人在家门绘凤图以避灾,有人在田头立小龛供奉“仁凰娘娘”。更有饥民聚集于旧祭坛前祈食,次日竟有商队误入此地,慷慨分粮。人们都说,这是“仁凰显灵”。
消息传至京城,朝中大臣惊怒交加,有御史上奏:“此女借赤凰余绪蛊惑民心,恐再生祸乱,请速缉拿!”
新帝览奏,久久不语。良久,提笔朱批:
>“昔有赤凰焚世,今有仁凰润土。火同源,性各异。不必追捕,任其行止。若天下太平,则无人信神;若民生艰难,则神自显现。与其禁声,不如省政。”
批文传出,百官默然。
与此同时,岭南某书院内,一位青衫夫子正执笔授课。堂下学子朗朗诵读:
>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……故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”
课毕,老者缓步走出学堂,立于溪畔柳下。春风拂面,柳絮纷飞。他仰头望着天空,似在倾听什么。
片刻后,他从怀中取出一只空铃,轻轻一摇。
无声。
但他笑了。
他知道,那声音已经传出去了。
某夜,他梦见敦煌石窟再度开启,凤凰展翅,飞越千山万水,最终化作点点星光,落入万家灯火之中。每一盏灯下,都有人在讲述同一个故事:关于一个布衣男子,负剑西行,踏碎谎言,唤醒良知;关于一个女子,继承遗志,行走荒野,播撒光明;关于一段被遮蔽的历史,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重生。
梦醒时,东方既白。
他提笔写下最后一章《守碑录》,藏于书院地窖铁匣之中,封皮仅书一行小字:
>“待后来者启。”
而后,他换下青衫,披上粗布旧袍,背上那只无鞘剑,再次踏上西行之路。
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在昆仑山巅观星三年,写下《天人纪》;有人说他混入胡商队伍,深入波斯腹地,只为查证赤凰信仰是否已蔓延海外;还有人说,他曾出现在安西都护府的一场大火中,手持铜铃立于烈焰中央,高声吟诵《礼运?大同篇》,直至火势自熄。
但所有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尾:
每当旱魃肆虐、瘟疫横行、官逼民反之际,总会有旅人声称,在荒原深处看见一道孤影。他(或她)或立于沙丘之上,或坐于残碑之侧,腰间铜铃轻响,声如细雨落地。
那一刻,风停沙静,人心顿明。
有人问:“你是谁?”
答曰:
>“我是不肯熄灭的光。”
多年以后,大周改元“景和”,天下承平已久。国子监修订《赤凰纪略》,新增一卷附录,名为《守碑考》。其中记载:
>“守碑人者,非常人也。或男或女,或隐或现,无名无姓,无始无终。其职不在护陵,而在护心。每当天道晦暗,人欲横流,必有一人自尘埃中起,负先贤之志,行孤绝之路,以身为薪,燃智火不灭。故史册不载其功,碑铭不刻其名,然百姓口耳相传,千年不绝。谓之:烬余有火,不在天边,而在人心深处,一点不肯熄灭的光。”
而在玉门关外,那座无名沙丘上的石碑,不知何时已被黄沙完全掩埋。
唯每逢月圆之夜,若有行人驻足倾听,仍能隐约听见风中传来低吟:
>“烬余有火,不在天边,
>而在人心深处,
>一点不肯熄灭的光。”
声音渐远,却又似从未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