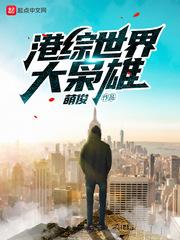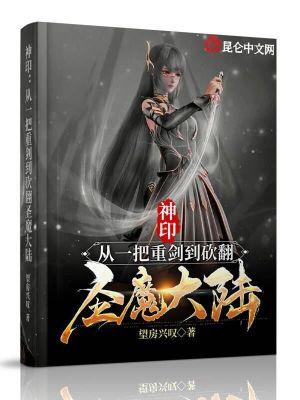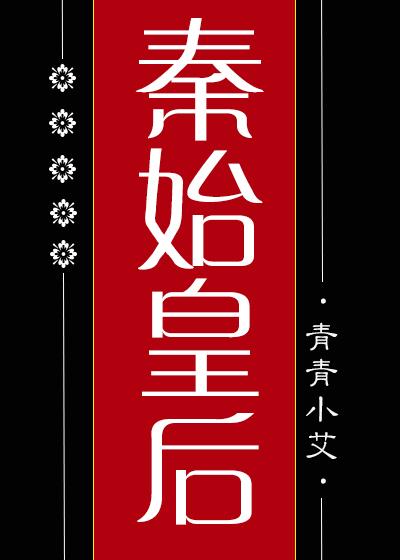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> 第四百零二章 天道好轮回(第1页)
第四百零二章 天道好轮回(第1页)
…
彻底控制住了金上京城中的金人了之后,宋江等人就更不客气了。
转天一大早,宋江就派户部侍郎胡直孺和原辽国旧臣萧庆入城,检验查看金国的各府库库存情况,并接管金国的所有文籍档案。
胡直。。。
雪后初霁,山色空蒙。老妇人坐化于鸣学堂废墟前的那一刻,天地仿佛屏息。她的身影渐渐被薄雪覆盖,如同大地轻轻合上一页书卷。那支骨笛静静悬在屋檐下,阳光照过笛身,映出一道微不可察的裂痕??那是百年前阿阮吹响第一声时留下的印记,也是时间无法磨灭的见证。
江南的春意却已悄然苏醒。苏州河畔,一名少女蹲在石桥边浣纱,手中布匹上织着细密的暗纹。她忽然停下动作,将布展开一寸,对着日光细看:经纬之间,竟浮现出一行极细的小字??“**她说的话,我们都听见了**”。这不是官府允许的文字,也不是哪家织坊的标记,而是无数女子世代相传的秘密针法。她抿嘴一笑,把布角折起藏进袖中,起身时瞥见对岸有个穿灰袍的老者正默默注视着她。那人拄着一根竹杖,面容清瘦,眼神却如古井深潭。
少女心头一跳,转身欲走,却被一声低语叫住:“你母亲可还好?”
她猛地回头,只见老者手中多了一支断笛,正用指尖轻抚其裂口。那一瞬,她认出来了??这不是影司通缉令上画过的脸吗?是那个传说中早已死去的“逆贼”零!
可眼前之人毫无杀气。他站在柳树下,像一株久经风霜却未曾倒下的枯木。他不再穿黑袍,也不再戴青铜面具,只披一件洗得发白的道袍,腰间挂着半块碎玉佩,随风轻晃。
“我问你母亲。”他重复了一遍,声音沙哑,“她是不是曾在织机旁教你说‘我不怕’?”
少女怔住。那是她五岁时,母亲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。那夜,官差闯入家中,烧毁了所有织物,只因母亲在寿被上绣了《归墟调》的曲谱。她亲眼看着母亲被拖出门外,却听见她在火光中高喊:“女儿,记住,哭也可以,但别忘了说话!”
她盯着零的眼睛,忽然发现那里面没有命令、没有冷酷,只有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温柔。
“你是……真的变了吗?”她颤声问。
零点点头,又摇摇头。“我不是变了。”他说,“我只是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。”
他转身离去,留下一句话飘散在晨雾里:“告诉春桃,第六声不是终结,是开始。我要去西域,把最后一面白幡立起来。”
与此同时,在西北戈壁深处,一场沙暴刚刚退去。牧羊女抱着那只早已长大的羊,跪在回声谷出口处的一片焦土上。这里曾是心音之核爆裂之地,如今只剩一圈圆形凹陷,中央矗立着一块无字石碑??那是四十九日前,阿阮消失的地方。
“她走了。”牧羊女低声说,泪水滑落脸颊,“但她把声音留下了。”
老琴师坐在不远处,正用断弦的琵琶拨弄一段新调。这旋律既不像《归墟调》,也不似任何已知乐曲,而是由风、沙、心跳与记忆拼凑而成。他闭着眼,手指颤抖,却坚定地弹下去。每一声都像是在呼唤,又像在回应。
突然,地面微微震动。
他们抬头望去,只见远方沙丘之上,缓缓走来一人。那人衣衫褴褛,拄着一根枯枝般的拐杖,左腿明显跛行,步履蹒跚,却走得极其稳重。她的脸上布满风霜刻痕,双鬓如雪,可那双眼睛??明亮如星,锐利如刃。
“阿阮!”牧羊女尖叫着冲上前去。
阿阮笑了,伸手抚摸女孩的脸颊。“我没走远。”她说,“我只是沉睡了一阵。当千万人齐声呐喊时,灵魂就会醒来。”
她望向那块无字碑,缓缓抬手,掌心贴上冰冷的石面。刹那间,石缝中泛起微光,仿佛有无数声音从地底涌出。那些光点升腾而起,凝聚成一行行文字,浮现在空中:
>春桃织布三年,传音万里;
>老塾师授童谣七百日,启蒙千人;
>鹰十九射落禁令三十六道,箭矢皆刻“听”字;
>林九渊之孙编纂民谣集十二卷,藏于百家灶台之下;
>大理道士观星破谶,以天象证人心不灭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