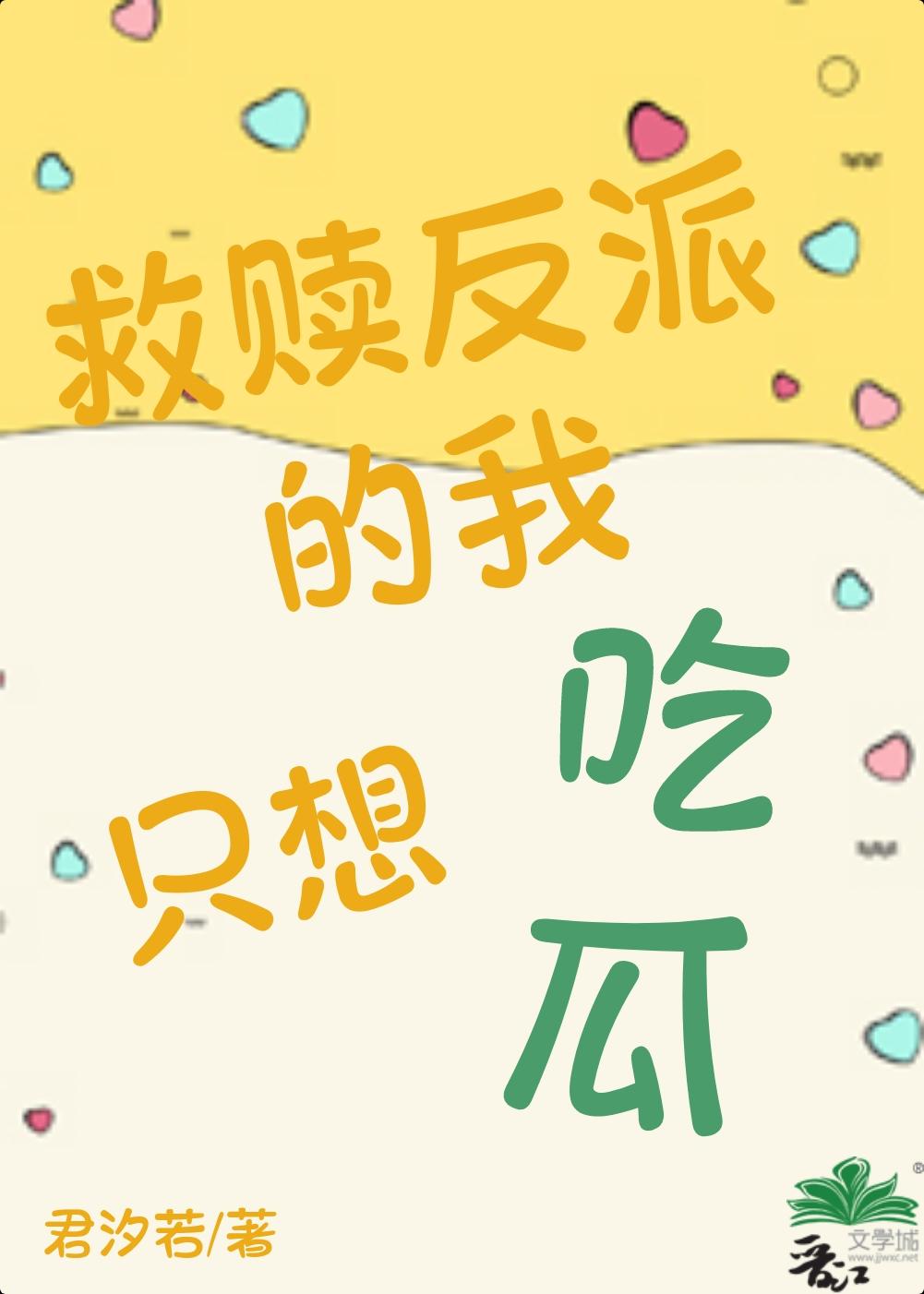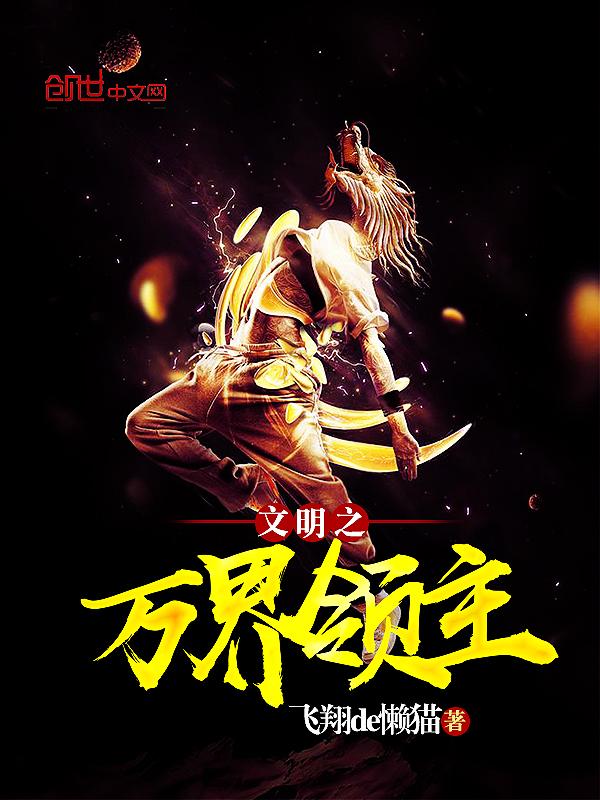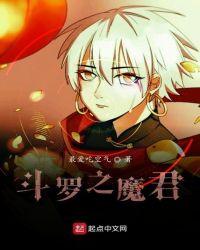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晋末芳华 > 第四百七十八章 一点尊严(第2页)
第四百七十八章 一点尊严(第2页)
她取出骨笛,放在唇边。
这是逆律器最后一次发声。
笛音未起,天地先应。冰川崩解,雪浪翻腾,整条裂谷如同竖琴被拨动。那声音不是空气传播,而是直接作用于物质结构,使岩石共振、水流变速、大气分层。方圆百里内的生物同时跪伏??狼群仰天长嚎却无声出口;鹰隼振翅却悬停空中;就连远处牧民帐篷里的铜壶,也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自行倾倒,水珠悬浮半空,排列成一行古字:
**“听!”**
这一声笛响,穿透时空壁垒,直抵人心最深处。
七日后,中原各地爆发大规模“失聪潮”。百姓纷纷报告再也听不懂官府公告、邻里交谈、市集叫卖。有人声称听到的话语全是倒放的录音,有人则坚称所有人说话时嘴唇动作与声音不符。恐慌蔓延之际,礼音监紧急启用“九重钟磬”,企图以正统雅乐恢复秩序。
然而钟声响起那一刻,全国范围内近万名曾参与“换耳游戏”的孩童集体昏厥。醒来后,他们无一例外地开始书写同一篇文本:
>“我们不是聋了,
>是终于摆脱了伪造的听觉牢笼。
>你们以为我们在模仿?
>不,我们在解码。
>每一次语气扭曲,
>都是对标准音轨的一次爆破。
>现在,轮到我们制定新的频率。”
与此同时,音骸城悄然出现在黄河故道。数百陶瓮随水流漂移,彼此碰撞发出奇异旋律。一名老乐师冒险靠近聆听,当场吐血而亡,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:“原来《太平引》的主旋律,是从三百个婴儿哭声中提取的痛苦基频拼接而成。”
消息传至宫廷,礼音监总监下令全国禁乐,关闭所有学堂音乐课,销毁民间乐器。他还颁布《净耳令》,要求百姓每日焚香诵《安神颂》,以净化耳道。
但讽刺的是,每当《安神颂》唱起,空气中总会浮现淡淡紫雾,雾中隐约有女子身影执笛而立。更有甚者,某些虔诚诵经者竟在梦中听见自己童年声音质问:“妈妈,为什么教我说谎?”
第十三夜,京城上空雷云密布。一道闪电劈开苍穹,击中太极殿顶的金兽鸱吻。火焰燃起瞬间,整座宫殿传出诡异合鸣??屋檐铜铃奏出哀乐,梁柱共振发出悲歌,连砖瓦摩擦都成了整齐的控诉:
“我们曾是谏臣的骨,铸成钟;
我们曾是忠烈的血,染成鼓;
如今却被用来歌颂暴政,
这是比死亡更残酷的凌迟。”
次日清晨,皇宫内外所有墙壁自动浮现耳形涂鸦,内部皆写同一句话:
**“你们听见的平静,是我们忍耐的极限。”**
林女并未停留。
她在共鸣石启动后便消失了踪影,只留下一枚脱落的青铜槐木之耳嵌在井沿。后来探险者发现,每逢月圆之夜,那耳朵都会微微转动,仿佛仍在监听某个遥远频道。
有人说她已融入风中,成为谢婉口中的“风语者”;也有人说她潜入地下,正在重建原始共振网络;更有传言称,她化身为万千声音的集合体,游走于每一个敢于质疑所闻之人耳边,轻声低语:
“你不一定要相信你听见的,
但你必须相信你有权怀疑。”
多年以后,一位年轻学者在整理敦煌残卷时,偶然发现一幅未标注年代的壁画。画中一名女子立于沙丘之巅,左手持骨笛,右手捧黑石,身后追随无数赤足男女,皆以手掩耳,面露痛苦却又坚定。壁画角落题有一行小字:
>“晋末有芳华,不在锦绣,而在敢疑之声。
>其香不传史册,却萦绕于每一次沉默的觉醒。”
他凝视良久,忽然觉得耳内一阵瘙痒。
回头望去,书斋窗台上,不知何时多了一片紫色花瓣,形如耳廓,正对着他轻轻颤动。
他知道,那不是幻觉。
因为这一次,他是主动选择不去听清它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