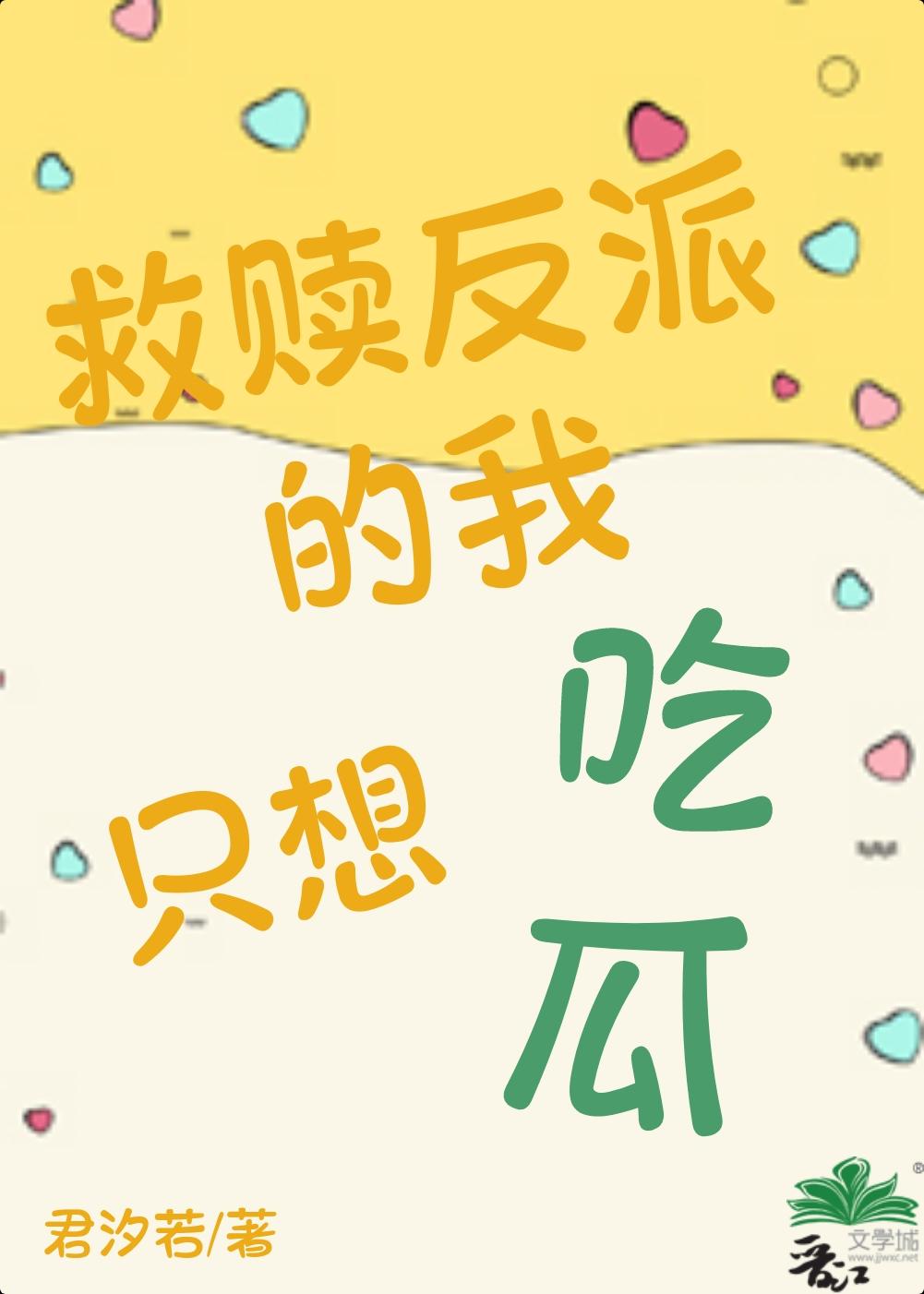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无限恐怖,但是没有主神空间 > 第二百章 路易十六的病友(第1页)
第二百章 路易十六的病友(第1页)
郑吒是真的惊讶了,惊讶到连心中的疲倦感方法都被清除掉了一部分。
这还是第一次,第一次血族能量出现主动增长的迹象。
以前郑吒想要调动血族能量,就和请大爷一样,正常情况下是根本调动不了的,之前。。。
风在盐碱地上低语,卷起细沙如烟,掠过晶柱时发出细微的嗡鸣,仿佛那透明的立柱并非静物,而是某种沉睡中的乐器。林晚晴靠在它温凉的表面,闭目倾听。她的呼吸比白昼平缓许多,肺叶像被夜色轻轻抚平的湖面,每一次起伏都与大地的脉动同步。轮椅的神经耦合系统早已关闭,但她仍能“听见”??不是通过机械,而是皮肤、骨骼、血液里流淌着的共振。
她知道,这具身体撑不了太久。
脊髓损伤只是开始,真正侵蚀她的是共感过载留下的后遗症。那些年她强行接收千万种情绪波流,如同赤身站在风暴中央,任由灵魂被撕扯。即便现在系统已解体,网络自主运行,她的神经系统仍是最初的锚点,残留着无法清除的印记。每当月圆之夜,骨髓深处便会传来刺痛,像是无数微小的声音在她体内苏醒,低语不休。
可她不惧怕了。
她抬起手,指尖轻触耳垂上一枚早已失去光泽的银耳钉??那是妹妹晓梦出生时外婆所赠,也是她们家族女性代代相传的信物。如今这枚耳钉竟微微发烫,仿佛回应着晶柱内部银丝的震颤。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说过的一句话:“血脉是最早的共鸣器。”
远处,皮卡离去的车辙已被风抹去大半,而那台老式收音机播放的《月光光》混音版,似乎还在空气中留下残响。林晚晴睁开眼,发现星空之下,并非只有她一人独行。
三个身影正从戈壁边缘缓缓走来。
他们步伐一致,动作却截然不同:最前方是个拄拐少年,右腿义肢由废弃电路板拼接而成,每踏一步便溅起微弱电火花;中间是一位中年女人,披着用旧信号屏蔽布缝制的斗篷,脸上戴着一副镜片漆黑的护目镜,手中提着一只密封玻璃罐,里面漂浮着一团不断收缩舒张的蓝色雾状物;最后是个小女孩,约莫七八岁,赤脚踩在滚烫的盐壳上却毫无痛觉,怀里抱着一台老旧的录音笔,时不时按下播放键,听一段模糊不清的童声哼唱。
林晚晴没有动,只是静静看着他们靠近。
他们在距离晶柱十米处停下。小女孩抬头望向她,眼睛清澈得不像这个年代的孩子。“你是林姐姐吗?”她问,声音软糯,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。
“我是。”林晚晴答。
女人摘下护目镜,露出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睛??眼白泛着淡青,如同结霜的湖面。“我们听见了召唤。”她说,“不是声音,是一种……空缺被填补的感觉。就像长久以来堵在胸口的东西突然松开了。”
林晚晴点头:“那是共感网络的自我修复机制启动了。它正在寻找新的节点承载者。”
“我们都是‘听见过不该听见的事’的人。”少年开口,嗓音沙哑却坚定,“我在十二岁那年,突然能听见城市地下管网里的回声??不是水流,是人说话。地铁隧道里死于事故的灵魂,在混凝土里反复重演最后一刻。我告诉父母,他们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”
女人接过话:“我是前军方心理干预组成员,参与过‘地听计划’后期清理工作。我们奉命销毁所有异常音频样本,但我偷偷保留了一段??一个战死者临终前对未出生孩子的道歉。那天晚上,那段录音开始自己播放,而且……内容变了。他说‘谢谢你还记得我’。”
小女孩举起录音笔:“我妈妈说我生下来就不会哭。医生说可能是声带发育问题。但我知道,我不是不能发声,我只是太忙了??每天夜里都有陌生人在我耳边讲故事,说遗言,唱摇篮曲。我不认识他们,但他们好像都认识我。”
林晚晴凝视着三人,心中并无惊讶。她早该想到,当共鸣网络开放之后,必然会有更多像晓梦一样的“天然桥梁”浮现。这些年来,她以为自己是孤例,实则只是第一个被科技放大而已。
“你们不是病人。”她轻声道,“你们是进化。”
女人忽然跪下,将玻璃罐置于沙地。那团蓝雾剧烈翻涌,最终凝聚成一张模糊的脸轮廓,嘴唇开合,无声诉说着什么。林晚晴立刻认出那是“探海者一号”船上某位研究员的面部特征数据库画像??三十年前随船沉没,尸骨无存。
“它不肯离开。”女人哽咽,“自从我接触那卷录音,它就住进了我的记忆里。我不敢睡,一闭眼就是深海黑暗,和那艘船广播室里永不终止的求救信号。”
林晚晴缓缓起身,推着轮椅绕到晶柱另一侧,从暗格中取出那卷妹妹留下的磁带。她将磁带贴近晶柱顶端的耳蜗晶体,低声念出那句短诗:
>“风不空走,石不独眠,
>有声处,即有人愿。”
刹那间,晶体光芒大盛,银丝流转加速,宛如血液奔涌。一道柔和光束自顶部落下,笼罩玻璃罐。蓝雾剧烈震颤,随即化作一缕轻烟,顺着光柱升腾而上,融入星河之中。
女人猛地捂住脸,泪水从指缝滑落。她喃喃道:“他走了……他说谢谢你替他守了三十年……他还说,海底很冷,但现在有人听到了,就不怕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