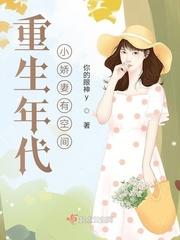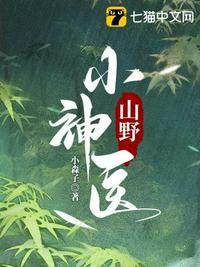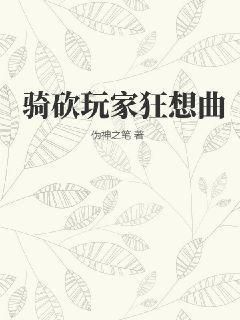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恋爱疗愈手册 > 第116章 廉耻凌晨还有一更(第1页)
第116章 廉耻凌晨还有一更(第1页)
黑色的蝴蝶结,佩戴在领口处的位置,很显然少女经过了好一番仔细的打扮,她栗色的长发披肩,只是略施粉黛的妆容,让其娇艳的简直不像话,配合上她身体那流畅和谐的线条,从少女身上简直挑不出一点儿瑕疵。
摇。。。
林小满把茶杯放在窗台上,阳光在水面上跳动,像一粒碎金。她盯着那封邮件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边缘。顾言的用词很小心??“不需要身份,不需要义务”,可正是这份克制,让她心里泛起一阵微妙的涟漪。
她不是没想过再见他。
但每一次念头浮现,都被理智轻轻压下。
她记得他说的:“等某一天,我们在街上偶遇,你笑着跟我打招呼,而我心里想到的不是‘她是我的前患者’,而是‘那个写博客的女孩,活得越来越好了’。”
她想成为那样的人。
不是靠一次讲座、一场重逢来证明什么,而是当她站在他面前时,眼神里不再有试探、依赖或未完成的情感投射,只有坦然与平等。
可这封邀请,像是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子,打破了她表面的平静。
她打开电脑,登录博客后台。昨天那篇《等待,也是一种成长》的阅读量已经破五万,评论区涌入了上百条留言。有人分享自己走出抑郁的经历,有人说终于鼓起勇气结束一段消耗型关系,还有人写道:“我也在等,等自己不再把爱当作救赎。”
她一条条看下去,指尖微微发烫。
曾经她躲在屏幕后,借别人的故事活下来;现在,轮到她成为别人的光。
可这光,真的足够明亮吗?
她望着阳台上的绿萝,叶片舒展,在晨风中轻轻摇曳。它曾枯黄过,被她遗忘在角落,直到顾言提醒她:“植物和人都一样,需要被看见,才能生长。”
她忽然意识到,这场讲座,或许不是关于“见他”。
而是关于“见自己”。
她点开附件,电子票上的座位编号是B区第七排,正对讲台中央。视野很好,不会太近,也不会太远。像是他特意安排的距离??恰到好处的亲近,又保有安全的边界。
她在姓名栏敲下自己的名字:**林小满**。
没有加任何称呼,也没有犹豫。
提交后,系统自动发送确认回执。她关掉页面,起身换衣服。今天约了心理辅导中心做最后一次复诊评估,主治医生会根据她过去三个月的情绪记录、社交功能恢复情况,决定是否正式结案。
地铁上人不多,她靠窗坐着,耳机里放着轻音乐。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匿名用户的新消息:
【我填了你的推荐书单,开始读《哀伤的记忆与重建的自我》。第一章就哭了。原来我不是软弱,只是太久没人允许我悲伤。】
她回复:【允许自己悲伤,才是真正的坚强。】
到达诊所时,走廊依旧安静。墙上挂着几幅抽象画,色调柔和,据说是艺术治疗师的作品。她坐在候诊区,翻着手里的《情绪日记》。最后一页写着上周的日志:
【今天独自去看了电影。散场时外面下雨,我没带伞,却没急着跑回家,而是站在屋檐下看了十分钟雨。雨滴打在水泥地上,溅起小小的花。我突然觉得,一个人的时间,也可以很丰盛。】
护士叫到她的名字。
走进诊室,李医生抬头对她笑了笑:“准备好了?”
她点头,把日记本递过去。
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,她们回顾了整个治疗过程。从最初几乎无法出门,到如今能独立完成日常事务、维持稳定作息、主动参与社交活动;从把所有情绪压抑成沉默,到现在学会表达需求、设立边界、接纳波动。
“你进步很大。”李医生合上档案,“尤其是情感独立这一块。很多人治愈后急于进入新关系,试图用‘被爱’来验证自己已经‘好了’。但你选择了等待,这很难得。”
林小满低头笑了笑:“顾医生说过,真正的亲密,是两个完整的人并肩站立。我不想再把爱情当成填补空缺的方式。”
李医生眼中闪过一丝赞许:“那你现在怎么看他?”
这个问题她想过很多次。
不是作为医生,不是作为拯救者,也不是作为潜在恋人。
而是作为一个曾深深影响她生命轨迹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