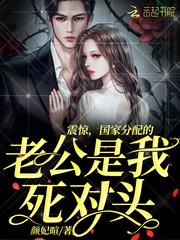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贫道要考大学 > 第194章 快放我下来(第1页)
第194章 快放我下来(第1页)
好在最后一科英语考得相对简单,大部分同学考完之后心情都很放松。
可惜明后两天还要上课,月考完也不放假,但一想到明后两天是校运会,这跟放假也没区别了。
考完试后,各班同学回到教室重新把桌子和。。。
清晨五点,城市尚未苏醒,只有环卫车在街角缓慢移动,像一头疲惫的牛。陈拾安坐在“倾听角”二楼的小厨房里,煮着一碗速食面。水汽氤氲上升,模糊了窗玻璃上的倒影。他没开灯,只借着炉火微光看着对面墙上那幅手绘地图??一百零八座倾诉舱的位置被红线串联,如同人体经络图上跳动的脉搏。
面刚出锅,手机震动起来。
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,没有称呼,只有一串坐标和两个字:“快走。”
陈拾安盯着屏幕看了三秒,立刻起身抓起外套。他知道这不是恶作剧。过去一个月,已有七座倾诉舱遭人为破坏:电路烧毁、录音模块失踪、外壳被泼红漆写着“蛊惑人心者死”。警方调查无果,监控全数失灵。阿岩私下查过,所有破坏发生前二十四小时,都曾有教育系统外包技术巡检人员登记出入记录。
他冲进录音舱区,迅速拔下主控机的数据卡塞进内袋,又将周默留下的U盘用锡纸包裹后藏进山桃树苗花盆底部。正要离开时,眼角余光瞥见舱门缝隙里夹着一张纸条。
展开一看,字迹稚嫩却用力:
>他们说我们的情绪是污染源。
>可如果心会痛,难道不是因为它还活着?
落款是一个代号:X-14。
陈拾安把纸条折好放进《火种法则》第十条旁边。他知道这是新的信号??“晨曦计划”的孩子们仍在试图连接。
外面巷口传来引擎低鸣。一辆黑色商务车缓缓停靠,车窗贴膜深得看不见内部。陈拾安熄灭屋内所有光源,从后窗翻出,沿着排水管滑下,消失在小巷深处。
六点十七分,阳光终于照进“倾听角”。那扇猩红的录音舱自动开启,仿佛昨夜一切从未发生。而此时,在三十公里外的一间地下会议室,“明路智能”高管团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
投影屏上滚动播放着《晨曦之下》的传播数据:全网曝光量破十亿,三百余所中学出现学生自发传阅《火种法则》的手抄本,甚至有重点高中学生集体拒绝参加“心理稳定性模拟测试”。
“不能再等了。”首席运营官敲着桌子,“高考只剩四十五天,‘云评估系统’必须如期上线。否则三年布局功亏一篑。”
“问题不在舆论。”技术总监推了推眼镜,“而在那个倾诉舱的离线协议。它绕过了所有数据采集节点,形成了真正的‘情感黑洞’。更麻烦的是,Z-09的异常投射证明,我们的共感通道存在逆向接入漏洞。已经有十二个测试体报告夜间梦见红色舱体。”
会议室陷入沉默。
片刻后,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女人开口:“启动‘回声清除计划’。”
众人侧目。
“不是物理摧毁。”她语气平静,“而是情感瓦解。我们要让公众相信,那些倾诉内容根本不是孩子的真实想法,而是被外部势力诱导产生的‘次生创伤表达’。具体操作如下:找一批家长出面指控‘归声行动’煽动子女背叛家庭;安排心理学专家发表论文,称长期匿名倾诉会导致人格解体;最后……放出一段经过AI重构的音频,内容是某个孩子哭着说‘都是陈拾安让我恨父母的’。”
“伪造录音不怕穿帮?”
“所以我们选一个真实存在但已失联的孩子。”她翻开文件,“比如周默。医院记录显示他目前处于保护性休眠状态,家人同意参与‘认知重建项目’。只要他一天不醒来,他就永远是我们需要的样子。”
话音落下,窗外雷声隐隐滚过。
同一天上午九点,S市第一中学高三(7)班教室。
李老师站在讲台前发放志愿填报指南手册,手微微发抖。昨天她接到通知,本学期“心灵成长课”将升级为“综合素质动态评估实训”,每节课需录制学生发言视频上传至市级平台。她的教案已被人工智能批注了十七处修改建议,其中一条写道:“建议减少开放式提问,避免诱发不可控情绪输出。”
下课铃响,一名女生悄悄递给她一张纸条:
>老师,我昨晚去了地铁站的倾诉舱。我说了真话,说我讨厌这种每天打分的生活。可今天早上妈妈翻我书包,发现了定位器APP的日志,问我是不是又去那种地方……她说要是再这样,就送我去封闭营。
李老师攥紧纸条,指甲掐进掌心。
她想起自己也曾是“晨曦计划”试点学校的年轻教师,那时领导说这是“教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”。她亲手提交过上百份学生情绪分析报告,换来了职称晋升和年度优秀奖。直到有一天,她在档案库里看到儿子的名字出现在“潜在焦虑倾向名单”中,关联标签竟是“母亲职业压力传导”。
她开始怀疑。
而现在,她知道不能再沉默。
中午,她戴上口罩走进社区医院旁的倾诉舱,录下人生第一段不带剧本的话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