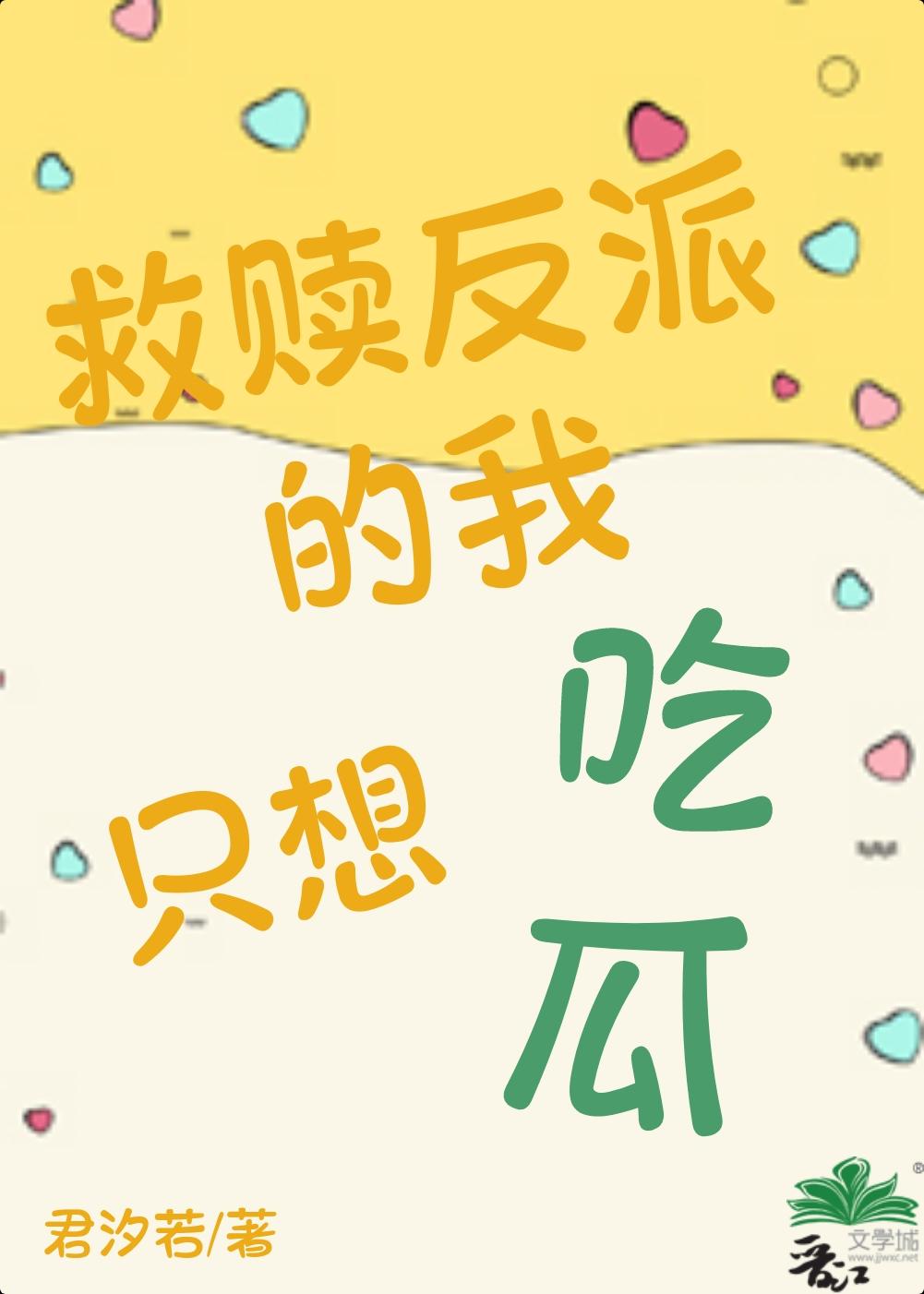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动物神探 > 第448章 你这不是野生大象吧(第1页)
第448章 你这不是野生大象吧(第1页)
潘文海一脸警惕。
提醒道:“沈新,你还是小心点儿。”
他看的出来,这头母象对沈新的态度不一样。
可再不一样,终归是一头野生的大象。
一旦发狂,现在也没有铁链锁着,谁能拦得住。。。。
夜色如墨,城市在霓虹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冷清。沈新独自坐在办公室里,桌上摊着一叠尚未归档的卷宗,最上面是付兰婷的供述笔录。他翻到最后一页,指尖停在那一行潦草却清晰的字迹上:“我以为她会恨我,可她从来没有……她只是叫我‘姨’,笑着叫我‘姨’。”
他的喉结动了动,轻轻合上文件。
窗外风声渐起,雨点开始敲打玻璃,像是某种遥远的叩问。这起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,但沈新的心里却没有一丝轻松。丁雨薇的名字从“病亡”改为“被害”,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已经实现,可那个四岁的小女孩再也回不来了。而周爱雪跪下的那一刻,不只是感激,更像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崩塌与重建。
他起身走到墙边,仰头望着那面锦旗??“动物神探”。这是去年市局年终表彰大会上群众代表送来的,当时他还觉得有些滑稽。毕竟他们办的是人命案,跟动物有什么关系?可现在想来,或许真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。
当年接手第一桩离奇死亡案时,是一只警犬在废弃仓库的角落里刨出了一个装有骨灰的陶罐;后来追查毒药来源,又是训犬队的老黄凭着气味追踪到郊区一处早已废弃的农药仓库;再往前推,连丁雨薇幼年住院期间的一段监控录像,都是因为一只流浪猫突然窜入镜头导致摄像头短暂偏移,才意外拍到了付兰婷提着保温桶进入病房的画面。
这些细节零散如尘,却在时间的沉淀中串联成线。
沈新缓缓坐回椅子,打开抽屉,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。封面上写着四个字:**异常行为记录**。这不是正式案卷,而是他多年来私下整理的一份特殊档案??关于人在极端情绪下的微表情、动作习惯、语言逻辑偏差,以及……动物般的本能反应。
他曾观察过无数嫌疑人,发现人在说谎或压抑仇恨时,眼神会不自觉地避开直视,呼吸频率变慢,手指蜷缩如爪,甚至走路的姿态都会变得类似受惊的野兽。而付兰婷在接受审讯前,在凉亭里抱着相框流泪的那个画面,被蹲守民警用长焦镜头拍了下来。她一边哭,一边用拇指反复摩挲相框边缘,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只死去的小猫。
“她在赎罪,也在享受。”沈新低声自语,“复仇完成了,痛苦反而成了唯一的陪伴。”
手机震动起来,是丁雨薇发来的消息:“我在医院拿到了林志远医生的手写补充说明,他已经签字确认当年存在诊疗疏忽,并愿意出庭作证。另外,人民医院同意为丁雨薇举行一次追思仪式,家属可以到场。”
沈新盯着屏幕良久,回复道:“告诉周爱雪,如果她想去,我会陪她一起去。”
放下手机,他忽然想起一件事??付兰婷被捕当晚,随身携带的那个旧相框里,除了丁雨薇的照片外,还夹着一张泛白的合影:三个年轻女人搂在一起,笑容灿烂。背景是老城区一家已拆毁的照相馆门前,牌子上写着“幸福影像”。
孙钊后来查过,那是2003年的夏天,郭美静、付兰婷和另一个名叫李慧芬的女人一起拍的。李慧芬,正是郭美静的亲姐姐,也是周爱华的大姑妈,也就是周爱雪的大姑。
但这张照片有个奇怪之处:三个人中,只有付兰婷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红绳手链,样式与后来丁雨薇戴过的那只极为相似。
第二天清晨,沈新驱车前往城南殡仪馆。天空仍阴沉着,细雨绵绵。周爱雪已经到了,穿着一身素黑大衣,头发整齐挽起,脸色苍白却不失镇定。她站在焚化室外的走廊上,手里紧紧攥着那份平反证明,目光落在远处一块空地上。
“她说过,等妹妹走了,就把她的骨灰撒在这片桂花树下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仿佛怕惊扰了什么,“可我一直没敢……我不敢让她一个人走。”
沈新默默递过一把小铁锹。
她摇头:“今天我不想埋她。我想……带她去看看这个世界。她还没活够。”
沈新没说话,只是转身走向车后备箱,拿出一个木盒。盒子里静静躺着一枚铜铃,铃舌上刻着一行小字:“愿你来世无忧。”
“这是我让师傅做的。”他说,“以后每年清明,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它去山里挂一棵树上。风吹铃响,就当是她在说话。”
周爱雪怔住了,泪水无声滑落。她接过木盒,双手颤抖,最终将脸贴在冰冷的金属表面,低低唤了一声:“妹妹……姐姐带你回家。”
回程途中,丁雨薇来电,语气急促:“沈新,你猜我们在付兰婷住处搜到了什么?不止是溴敌隆的购买记录,还有整整八年的日记本!”
“念。”
“2006年11月5日,晴。今天她吐血了,护士说是肿瘤恶化。没人知道是我加的量多了半勺。她妈哭得像个疯子,可她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干净……我受不了了,我又给她减了药。但她还能好吗?我不知道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