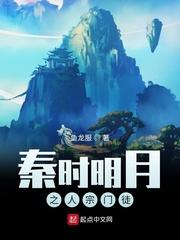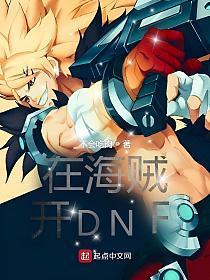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循规蹈矩能叫重生吗? > 310 她的价值(第1页)
310 她的价值(第1页)
周明远的做事风格,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。
先发制人。
习惯掌握主动权的他,从来不喜欢被动猜测。
于是,周明远直接开口,笑着把视线向戴颖那边投了过去。
“戴姐啊。。。。。。”。。。
雪后的清晨,空气清冽如洗,共耕园的菜畦上覆着一层薄霜,像撒了糖粉。杜佳诺踩着结冰的小径走进厨房时,母亲已经炖上了第一锅高汤。砂锅盖边缘冒出细白的蒸汽,一缕缕缠绕在老旧的吊扇叶片间,仿佛时间也慢了下来。
“今天要试新配方。”母亲头也不抬,正用木勺轻轻搅动汤面浮起的油星,“我把腊肉换了熏鸭腿,加了点陈皮和山药。你说老张叔上次来吃得直抹眼泪,说这味儿让他想起知青那会儿,队里妇女偷偷塞给他的一碗鸭汤。”
杜佳诺笑了:“那就叫‘知青鸭汤’吧,写进下一期菜单。”
她蹲下身检查橱柜里的调料罐,忽然摸到一个陌生的小布袋,解开一看,是晒干的野葱花,还带着山野的气息。“这是哪来的?”
“李桂芳从贵州寄来的。”母亲接过袋子闻了闻,眼角微弯,“她说那边山沟里的妈妈们学会了做酸汤鱼,顺手采了些野葱晒干送我,说是‘回礼’。”
杜佳诺心头一热。她打开手机,翻出李桂芳前天发来的照片:一群穿着苗绣衣裳的妇女围坐在火塘边,锅里红汤翻滚,孩子们蹲在一旁剥毛豆,脸上沾着辣椒粉,笑得灿烂。配文只有一句:“我们也有‘妈妈的味道’了。”
她把照片设成了屏保。
上午十点,第一位客人到了。是个穿灰呢大衣的男人,拎着一只旧藤篮。他没看菜单,只是轻声问:“能做一道萝卜炖牛腩吗?要放两片生姜,不放八角。”
林晓雯认出了他??是三个月前那位因女儿车祸去世而崩溃的父亲。那天他坐在角落,盯着一碗空面碗看了两个小时,一句话没说。后来他每周都来一次,每次都点同一道菜,但从不碰筷。
“您想自己做吗?”林晓雯轻声问。
男人点头,眼眶泛红:“她……我女儿十一岁,最爱吃我老婆做的这道菜。去年冬天,她妈走得太急,连菜谱都没留下。我想……试着还原它。”
林晓雯带他进了教学厨房,调出数据库里相似口味的配方,又请来擅长家常炖菜的陈玉梅协助。三人围着灶台,一次次调整火候、水量、香料比例。男人的手一直在抖,切萝卜时差点割伤手指,却被陈玉梅轻轻握住:“别急,你老婆当年一定也是慢慢学会的。”
第四次试做时,汤刚冒泡,男人忽然停住动作,深吸一口气:“对了!她总爱在快出锅前撒一把青蒜末,说这样才有‘活着的味道’。”
他们照做了。揭开锅盖那一刻,香气扑鼻而来,男人猛地捂住嘴,肩膀剧烈起伏。
“就是这个味儿……”他哽咽着,“她回来了。”
他盛了一小碗,摆在厨房角落的空椅子上,轻声说:“囡囡,爸爸找到了妈妈的味道。”
那天下午,杜佳诺把这段录音转成文字,贴在“故事交换角”的新位置,标题是《活着的味道》。旁边摆着一小碟青蒜末,纸条写着:“请为想念的人撒一把。”
入夜,长沙新店的施工团队发来直播链接。外墙最后一块瓷片已安装完毕,整面墙在灯光下熠熠生辉,如同一条流动的母亲河。镜头缓缓扫过那些名字:王秀英、李桂芳、陈玉梅……最后定格在“黄阿婆”三个字上。
杜佳诺记得黄阿婆。她是去年冬天来的,佝偻着背,提着一罐自家腌的雪里蕻。她说儿子在国外多年未归,怕他忘了家乡味,求食堂帮忙录一段视频教他做饭。“我不识字,只会做这个。”她搓着手,声音微颤。
当时是小满帮她拍的。孩子踮着脚举着手机,一句句念出台词:“第一步,把雪里蕻泡水两小时;第二步,挤干切碎,用猪油煸香……”黄阿婆一边做一边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期待。
三个月后,他们收到一封海外来信,附着一张照片:异国厨房里,一个中年男人端着一碗雪里蕻炒肉丝,背景是飘扬的中国国旗。信上写道:“妈,我终于吃到了家。”
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告诉黄阿婆,她就在春天来临前走了。
如今,她的名字刻在墙上,像一颗沉默的星辰。
杜佳诺拨通林晓雯的电话:“把那段视频找出来,做成二维码,贴在‘黄阿婆’名字旁边。以后每位看到她名字的人,都能听见她的声音。”
“已经在做了。”林晓雯说,“还有人提议,让家属录一段语音留言,扫码就能听。比如‘爸,今年清明我带孙子来看你了’。”
杜佳诺闭上眼,仿佛看见无数声音在城市上空交织,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,兜住所有失落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