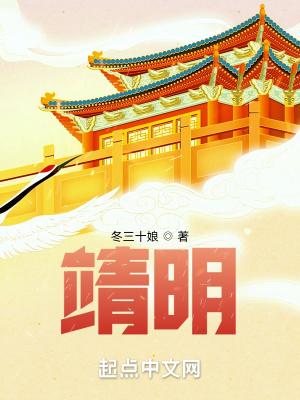恋上你中文>娘子,别这样! > 第575章 造反了玉衡之殇八千(第1页)
第575章 造反了玉衡之殇八千(第1页)
深夜。
躁动不安的北风笼罩着整个皇宫。
洛天权叹息着,瞧瞧他们洛家这些皇帝的下场,隆泰帝一代武帝,上马杀敌下马治国,最后却因落水,感染风寒不治而亡。
元景帝,做皇帝还不足十年,前些年。。。
八月初七,长安城晨雾未散。
宁平的马车穿过朱雀门时,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。青石板路湿漉漉地映着残灯余烬,仿佛昨夜万人守灯送别的烛火仍未熄灭。街道两旁的屋檐下,仍有百姓悄然伫立,手中紧握九心莲干花,不言不语,只以目光相送。一名老妪跪在阶前,将一碗清水置于门槛外??那是北方民间最朴素的迎魂礼:**“水净路,好归途。”**
宁平掀帘望去,眼眶微热。他知道,这已非一座冷漠的帝都,而是一颗正在苏醒的心脏。每一盏熄灭的灯、每一片飘落的花瓣、每一句未曾出口的叮咛,都在为记忆筑基。
御史台派出的监察使早已候在昭文伯府门前,身披黑袍,面无表情。他们查验随行物品,连宁平贴身携带的一枚旧铜铃也被取走登记。柳芸派来的书童欲抗议,却被两名禁军按住肩膀压跪于地。宁平抬手制止争执,淡淡道:“让他们查。真正的记忆,藏不住,也拿不走。”
他缓步走入新赐宅邸,庭院空旷,雕梁画栋皆崭新如纸,唯独缺了人气。正堂悬一幅空白卷轴,据说是皇帝亲命挂上的??意在提醒:**你所得之位,尚未书写功过。**
当晚,宁平独坐灯下,取出袖中残片,正是那日乞丐怀中的《共生识论》抄本一角。他轻轻摩挲页脚上“张守仁”三字,提笔补全一段批注:
>“姓名者,人之根也。断其名,则斩其脉;记其名,则续其魂。张守仁,河北枣强人,父张大牛,祖籍可溯至永乐年间屯田戍卒。此人虽贫贱不闻于世,然其志比昆仑雪更洁,其心比苍梧井更深。吾以玉碑之名铭记:此子,乃共忆之始灯之一。”
写罢,他将纸片焚于灯焰,灰烬投入院中古井。片刻后,井水泛起涟漪,竟浮出一圈微光,宛如星图流转。
与此同时,皇宫深处,拂尘老太监被锁于冷宫柴房,口中塞布,双手反绑。但他双目炯炯,嘴角含笑。夜半三更,忽有鼠群自墙缝钻出,围绕他足边盘旋不去。其中一只灰毛小鼠口衔半片枯叶,叶上墨迹斑驳,依稀可见“共忆”二字。
老太监奋力挣开嘴中破布,低声道:“去吧……告诉他们,我在等信号。”
小鼠倏然窜出窗缝,消失在月色之中。
翌日清晨,礼部送来首批审定教材名录。名单上,《共生识论》赫然列为“待勘本”,须删去“禁忆者弑神”“民不可欺”等十一处“悖逆之语”方可刊行。随文附有一纸密函,署名为“周厉”,言辞冰冷:
>“昭文伯当知进退。爵位可赐,亦可夺。若肯配合监察司修订典籍,三年后或可放还昆仑。”
宁平冷笑,提笔回复仅八字:**“我修的是心,不是旨。”**
他命人将原版《共生识论》拓印百册,暗中交予慧贞安排的宫女线人,藏于绣鞋夹层、食盒暗格,逐日带入内廷。更有巧匠依样打造十二枚hollow铜簪,内部中空,嵌微型竹简,刻录《万忆图》支脉信息,由女官插发戴用,通行无阻。
与此同时,苏婉儿在南方发动“千灯计划”。她亲赴江南十八镇,召集绣娘、说书人、走方郎中、茶肆掌柜,组成隐秘传讯网。药方纸上暗藏密码,评弹曲词里埋着线索,甚至连孩童跳绳歌谣也被改编成记忆密语:
>“一念不忘爹娘恩,
>二更不睡抄家训,
>三声钟响思正台,
>四海同哭失亲人……”
这些歌声顺着运河一路北上传至汴梁,又被货船捎进幽州。戍边将士听后纷纷私录成册,在哨塔夜巡时低声传诵。某夜风雪交加,一位老兵突然嚎啕大哭:“我想起来了!我娘不是病死的,是被拖去断忆炉前活活烧瞎了眼睛啊!”
消息传回长安,周厉震怒,下令彻查“妖音惑众案”。然而越是封锁,民间越是以沉默回应。洛阳一家酒楼一夜之间所有客人用餐完毕后齐齐放下筷子,静坐一刻钟,然后默默离去。掌柜不解,问其故,一人答曰:“我们在替死者吃饭。”
此事迅速蔓延,称为“默食潮”。全国三百余城出现类似场景,甚至有整条街市同时熄灯闭户,只为完成一次集体追忆仪式。
宁平得知,仰望夜空长叹:“他们终于学会了不用声音说话。”
九月初九,重阳登高日。
朝廷照例举行秋祭大典,百官齐聚太庙。周厉特意安排一场“清心仪式”,请来三位高僧诵《忘忧经》,意图冲淡民间对“记得”的执念。香烟袅袅升腾之际,忽然一阵狂风破殿而入,卷起供桌黄绸,直扑主龛。
那块象征皇权掌控记忆的“断忆诏书”残片,本已烧毁大半,仅存一角封于琉璃匣中,此刻竟自行裂开,灰烬飞扬,在空中凝成四个大字:
>**你还记得吗?**
满堂哗然。皇帝脸色煞白,踉跄后退,撞翻香炉。火焰落地未灭,反而沿着地面蔓延,勾勒出一幅巨大地图??正是《万忆图》轮廓。数十名年迈官员当场跪倒,痛哭流涕:“老臣当年奉命销毁族谱……罪该万死!”
唯有周厉standing不动,咬牙切齿道:“幻术!必是宁平施法作祟!”
他转身欲命禁军搜捕昭文伯府,却发现随行侍卫中有七人悄然摘下头盔,露出额前刺青??一朵盛开的九心莲。那是“共忆会”最忠诚的死士标记。
“你们竟敢背叛朝廷?”周厉怒吼。
为首之人平静回答:“我们从未效忠遗忘。”